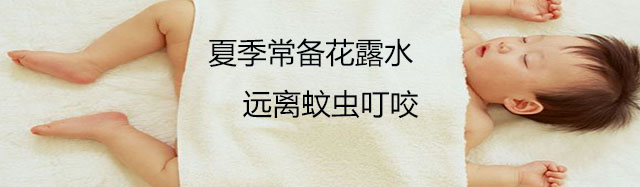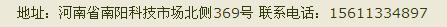多学科思维基诺族文化形态稳定性的历史自然
西双版纳地理物候与文明形态
所谓的文明就是自然界不再给人类提供生存资料,人类的一切生活资料都需要人类自备。西双版纳地理物候与文明形态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研究文明发展史的时候,提出一个极具建设性的理论。他认为从推动文明的角度看,环境不能太坏,也不能太好。太坏,人类无法发展,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但环境也不能太好、太优越。太优越了,人们不需要勤恳劳动,懒得去奋力开发,也创造不出什么东西。最好是在一个适度的水准上,既有适宜的基础,又存在一定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会不断地受到激励(去应战),向环境的深度开发,文明于是不断发展。
对于太好的环境,为什么不能给创造出农耕文明文明,我们举例来说,比如在我国的一些亚热带地区,气候温热,雨量充沛,于是植被繁茂,第一层多为草本植物,第二层为灌木层,第三层是数十米高的乔木密林。由于它生存资料天然生活资料丰富,因此古人在之前是根本用不着开发农业文明。第二个原因是如果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发展农业文明,有其主要的制约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远古时代,古人只有一把石斧,如果今天给我们一把钢斧,也未必能够开发出大片的适合农耕地带,即使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大树,我们也未必能完全清理其根部。如果古人用石器工具,可能几个月都不能完成清理一颗树的工作,何况是热带地区一亩地都有成片茂密的高大乔木,古人在一年都可能无法完成。即使开垦出来一亩地,也任然种植不了庄稼,因为周边的高大乔木会挡住阳光,他仍然只能长草。
这就是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不能成为农耕文明发祥地的原因。
我们再回看我国西双版纳地区,由于太阳入射角高,冬至时分高度角最低为45°,所以热量丰富,终年温暖,四季常青。具有“常夏无冬,一雨成秋”的特点。一年分为两季,即雨季和旱季;雨季长达5个月(5月下旬—10月下旬),旱季长达7个月之久(10月下旬—次年5月下旬),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本区热量丰富,终年温暖,四季常青。又因距离海洋较近,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控制和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常年湿润多雨,所以森林繁茂密集,植物繁多。这也是我们西双版纳地区农耕文明不能发生的重要原因。
由于该地区多山多果,以至于在远古时代到民国时期,很多民族都依照延续了狩猎采集的文明形态,至今很多民族依然保留了狩猎采集文明形态下的遗风与遗俗。
基诺族文化形态—婚恋观念
比如,在西双版纳基诺族乡,我们通过对基诺族各村寨的考察表明,基诺族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前母系制的血缘婚遗风,氏族内男女虽然不能结婚,恋爱却不被阻止,包括同居。时至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基诺社会中婚恋的五个特征在于:
其一,婚姻恋爱自由,不由父母包办;
其二,恋爱双方年龄相当;
其三,恋爱的三个阶段反应了人类性爱的一般自然过程;
其四,婚姻缔结的基础是性爱,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其他;
其五,从恋爱到婚姻,双方主体有一系列相互考验的步骤,并有充分的自由选择余地。基诺社会不会太重视“童贞”的说法,对恋爱期间的同居也有着较为宽容的态度,即便是经过同居最后没有结婚或者是离婚,男女双方也不会有类似被抛弃、被遗弃或者痛不欲生的感觉,更不会以此为“辱”,旁人也不会因此投来异样或者同情的目光。在他们看来,这是较为正常的意见事情,只要是两人已经不再有感情,不再情投意合,不在一起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
在程序上,离婚也不如现代社会中那样复杂,“只要在一块喝喝酒,将结婚时作为结婚见证所收藏的三两三钱瓷碗片抛撒出门即可”。基诺男女都在平静的接受着对方的选择,并给对方最大的自由与权力,彰显了男女在性及婚恋方面的平等。正如牛江河所言:“在基诺族的人格观念中,个人属于个人自己,个人具有个人人格,个人是各自独立的,个人对自我有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恋爱自由自主,结婚自由自主,生育自由自主,离婚自由自主。”正是这样在血缘婚遗存的基础上,且强调自我,相对自由、独立与宽容的婚恋文化基调。
长期以来,基诺族居住于山林中,与外界少来往,靠打猎、挖野山药、摘棕榈树果为生,在农业生产方面刀耕火种是基诺传统社会的主要生计方式。由于居住地域有限,环境并不是十分恶劣,造成相对平衡均匀的男女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在传统基诺社会中,基于生计方式的社会分工并没有给男女在劳动分工上造成巨大的、不可弥补的差距。
只有那些需要强体力的劳动只有男性参加,此外的各种生产劳动,比如现在的割取橡胶、采摘茶叶等等。这是基诺族人在日后社会性别的自由选择方面十分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并且提供了一种十分有利的空间。长老对家族婚姻的管理,虽也有禁止氏族内婚的习惯法,但又有这样一条变通的办法:一对相爱的同一血缘氏族的男女如欲结婚,只要举行一个认其他氏族的长者为干爹的办法,便可得到习惯法的许可,达到结婚的目的。
可见,即便是主事的长老对婚姻的干涉力度和影响力也始终有限,不然在不允许氏族内通婚的部族,不会出现因氏族内通婚人群就产生出为此变通的习惯法。家庭及社会的对个体所进行的文化濡化,从婴孩的出生便已经开始,对个人的性格习性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
社会性别理论强调的就是人的性别认同是经由后天塑造而成,并非天生的。大部分社会都将人的性别限定在非男即女上,而且围绕着男女生理特征的不同制定了两套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规范。然而,在基诺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孩子是老天赐给的,无论男孩女孩,都是宝贝。且是神的意志,不可违抗”。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导致在男女差异的塑造上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刻意与强烈。与民族发展程度和经济情况相似的布朗族相比,在基诺族的传统教育理念中,男女性别平等的观念明显强于布朗族。作为一种教育的惯习,基诺族对人性的尊重,对当下基诺社会中人们的性别观念及性的实践产生着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在基诺族社会,性少数群体占有一定比例,且被单独划分为一类用基诺语称作“考卜拉”。“考”即“人”的意思,“卜拉”是“变掉”的意思。在这里“考卜拉”的本意指的是除异性恋者以及拥有异性婚姻之外的一切人的总称,具体来看又包括了男性“考卜拉”(即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女性“考卜拉”(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又被称为“考忒”),没有结婚的女人,以及一些易性者,这3类较为特殊的人群,如果夸大其外延,则包括了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恋者,可以现代意义上的LGBT人群对应。
上世纪50年代基诺社会尚存“考卜拉”。当时在上千人的基诺山上生活着数十个“考卜拉”,他认为基诺族社会同性之间的爱情是普遍的。现今,在调查的村寨中,当年杜玉亭书中所提到的者不勒和白腊约、乍什和法耶、白腊则和白腊约、白佳林和先卜拉等原有的“考卜拉”,只有白腊则和白腊约仍健在,他们算是老一代的“考卜拉”。相比于其他社会,基诺族社会中性少数群体不仅在数量上人员较多,情感模式与关系比较复杂。“白腊耶”和“白腊约”是一对至今已经70多岁且仍健在的一对女同性恋者。二人自成年礼后就同居,直到现在也未分开,一生从未与男性性接触。另有一对同性恋人,二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后来他们先后与异性结婚,但二人依然来往密切。在村社喜庆宴会时,两人并肩而坐,形如夫妻。如果二人相互串门,晚上住下时,妻子会主动给他们让出床位,他们同睡一床。在基诺族传统社会中,同性恋爱与异性恋爱都是自由的,同性恋和异性恋同时享有正常的爱情权利,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由长老们在尊重当事人爱情权利的前提下出面调解,并且礼俗还在相当程度上是尊重和保护同性恋的巧。时至今日,随着公路的修建以及村级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基诺山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更为方便,交往范围也更广泛。除原有的“考卜拉”之外,又有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考卜拉”发展出来,部分还组成了同性家庭,甚至出现了易性者等新形式的“考卜拉”。可以说,“考卜拉”是基诺社会特有的,难得一见的以尊重性少数群体选择的文化现象。以下笔者对“考卜拉”文化的详细考察将从一对女同性恋的日常生活开始。
“考卜拉”的实践:一对基诺族性少数的日常生活在美丽的基诺乡山寨里,“考卜拉”的故事却还在延续着。丽和君的故事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也是调查过程中接触最为频繁的两位“考卜拉”。在初见她们时,她们与普通夫妻无异,君在两人居住的小院中刷牙,丽在喂鸡,屋子里的音响开得震天响。君有1.65m左右的个头,精炼的短发,穿着粉白相间的男式条纹衬衣,外面还套着一件白绒背心,脚上一双人字拖,看上去颇似男人,但又比男人瘦小很多,声音也清脆。丽也有1.65m,身穿黄色花纹短褂,下面齐膝短裤,也着人字拖,但她皮肤黑黑的,声音也粗糙,身体明显发福,看上去比君要壮。她们之间情感的经历与故事,不仅可以让我们瞥见基诺社会中“考卜拉”群体的生活现状,是她们日常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更能让我们对基诺文化中固有的关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以及对待性少数群体的文化态度及惯习有更进一步的认知与了解。
(一)从“异性”到“同性”的叙事丽与君相识于小的时候,她们的故事是从同性的友谊开始。据君说,最早认识丽是在丽七八岁时。当时君的哥哥在新寨做上门女婿,她不时会去哥哥家。一天,看到了扎着两个小辫子的丽和伙伴玩得很开心,但那时比较羞怯,并没有主动去打招呼。年,君到新寨参加小学毕业考试,两人同在一个考场,从此二人相识。但考试完后,并未再联系,直到年两人重逢于老寨的露天电影场。从此二人相熟起来,并经常一起看电影,有时看完太晚丽就会在君家宿下,一来二去,两人之间几乎无话不谈。直到年,君与老寨生产队队长杰谈起了恋爱,据村民说,君采完茶叶后到杰那里称重量,君当时留着长头发、面容清秀、干活勤快、手脚利落、对人热情,同时杰也是一个活泼幽默的优秀男青年。4年后,也就是年,君与杰结婚了,当年便就有了一个女儿。在此期间,君与丽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人也会进行换工。年,丽也与同村人结了婚,办酒席时君背着一岁多的女儿也去了。此后君和丽又各自生了儿子,因为各自都有了家庭,两人也就少来往了,走在路上会打招呼,从好朋友转化为普通朋友关系。转折源于二人的原先所组成的异性家庭关系的恶化。在的家庭中,君和丽的家庭生活并不尽如人意。杰是村里的干部,开会与出差的机会很多,通常去就是好几天,家务活和地理的活都是君一个人干,同时君还要负担养育两个儿女的职责,日子过得比较辛。丽的丈夫性子温和,但是有些木讷,脾气也古怪,和丽闹别扭后,从不主动言和,总是丽主动和丈夫说话言和,丽带着两个儿子,拖着沉重的家庭负担,让丽患了风湿病,并从此落下了腿疼的毛病。年的除夕,丽回忆说:“过年那天我家杀猪,邀请君来我家过年,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喝了点酒,晚上君在我们家住下了,我老倌(“丈夫”的意思)也没说什么。我担心她一个人睡害怕,就和她一起睡。这天晚上,我们就发生了性关系。”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而生活再也不能平静了。虽然二人平日里依旧在与各自丈夫组成的异性家庭里进行生产与生活,但是交往又频繁起来。利用换工的机会,丽经常到君家里帮忙采茶叶和割胶,君有时也到丽家帮忙,两人同吃同睡,甚至会穿一样的衣服,也就是情侣装,遇到农闲,两人经常结伴出去游玩。虽然原本的家庭还在维系中,但君的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缺失。
年,在与丈夫杰发生了一点争执之后,君选择在第二天到乡政府民政所与丈夫办理了离婚。离婚时,他们的两个未成年的子女儿选择跟着杰一起生活,其他财产则均平均分配,主要有橡胶林、茶叶地,还有其他钱粮财物、牲畜等等。此后,君带着自己名下的各项财产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庭与妈妈、哥哥一起生活了一年,次年她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在附近建盖了属于自己的一室一厅落地式瓦房,持有个人户口簿,独立成为一户。盖房时,丽为君提供了一千元钱的资助,并亲自帮忙参加了建房过程。在君离婚后,丽与家庭的关系也并未得到改善,一边要带孩子一边要忙于农活的丽请求公婆照看小孩,但是遭到公婆的拒绝,丽与公婆的关系原本就不好,此次更为恶化,甚至升级为恶语相加,加上丈夫在其生病期间对她的不闻不问让丽对家庭的期望彻底化为乌有。经过几天的考虑,丽决定搬到君家,与君同住。同时几乎断绝了与原来家庭的所有联系。之后几个月里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由此,君与丽组成起了属于她们自己的“新家庭”。
(二)“新家庭”亲密关系的构建自从住到一起之后,君和丽便共同精心打造起两人的居所。君和丽房子前面有个小院子,院子与水泥路之间用竹编的栅栏隔起来。院子里靠近水泥路边有一个安装了太阳能的小型卫生间,与卫生间一墙之隔的是矮小的猪圈,猪圈里没有猪,而是放着收橡胶用的塑料桶。房子右边的空地上有一个低矮的柴房,架子上堆满了干的柴火。院子左边的角落上有一个小小的鸡圈,几只小鸡仔在地上叽叽喳喳地觅食。房子后面是一个高的坡坎,坡坎上种了几十株李子树,开着细碎的白花,在雾气迷漫的早晨里安静得如小家碧玉一般。房子是一个平层,四周板壁是用编好的竹排、粗加工的长木板和破旧的门板围起来的,顶上铺着黑色的挂瓦。在屋子的左边,火塘上架着铁三角架,边上放着柴火,两口大铁锅靠在板壁上,角落周围的板壁被烟熏的黑黑的。饭桌左边有一个竹编的板壁把卧室与外厅隔了开来。现今她们已经公开的以夫妇的名义在村子里生活,也形成了一致对外的关系。她们之间互相以基诺语中的“老公”与“老婆”相称,而且对于情感的经营自由她们的方式。在一起生活的四五年时间,她们对现在的生活还比较满意,最有意思的是两人还过起了纪念日。
君说:“年2月6日是我们认识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我们要买酒杀鸡。去年喝了三件啤酒,杀了两只鸡,叫来几个人一起庆祝。”
丽说:“刚来那段还是会想回家,有点后悔,但是又不敢回去,很尴尬,但是她对我太好了……现在不后悔了,过一天算一天,只要快乐就好。”相对来说,在两人的关系中,君显得比丽主动,也更认可这段关系,君说:“我现在觉得很满意,没有她(指丽)我一个人活不下去,我们相互依赖。”
丽说:“说不上是依赖,我们互相扶持,走一步算一步,能过一天是一天,不想以后。”当然有时也会磕磕绊绊。年1月30日,丽从君那里回去以后,好久没有回来,君急了。那时两人都有了手机,君就经常打电话发信息给丽,丽很少接电话和回信息。丽说:“那时我家在10公里外,她天天打电话给我,一打就哭,后来我就不接了。后来我又回到了君的家1次,她在家喝了三件啤酒,还打烂了一个板凳。”对于这次事件,君腼腆地笑着对笔者说:“她不回来,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天天喝酒,如果她不回来,我今天就不在了,或者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丽看了君一眼说:“她对我太好了,我舍不得丢下她一个人。”
(三)性别角色的分工与塑造在君和丽的同居生活中,家庭劳动既有分工也有协作。在家庭劳动中,君承担了大部分重的劳动,如上山下山负责搬运、拿工具和重的东西,在家里修灯泡、厕所、杀鸡等,承担了一个家庭中丈夫的角色。相比之下,丽的劳动比较轻松,一般是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如扫地、刷碗、洗莱做饭等,同时也参与采茶、割胶和摘李子等劳动。平时家里的生活用品是两人一起去买的,并实行AA制。
君在穿着上有强烈的男装倾向。君喜欢条纹或者格子衬衫,喜欢扎腰带,风格很男性化。君说:“我不爱穿女人衣服,穿男的衬衣和裤子舒服,她买的衣服我不喜欢。”君的衣服大都是衬衣,腰间常扎着腰带,脚穿褐色运动鞋,嘴里常常吹着口哨,这是君的日常装扮。劳动时,君总是头戴红色鸭舌帽,身上穿着浅蓝色牛仔夹克,腰间扎着一把小砍刀或者是启上扛着两把砍刀,打扮如当地的基诺族男子一般。丽背着一个小挎包,包里有水、烟、打火机之类的小物件,亦步亦趋地跟在君的后面。丽喜欢颜色鲜艳一点的、风格比较女性化的衣服。丽回应:“她买的衣服我也不喜欢,我喜欢好看的、颜色亮一点的。”不仅衣服风格不一样,就连两人用的手机款式也是大相径庭,君的手机是金黄色宽屏直板手机,这种手机在市面上基本上是男人在用。丽的手机是粉红色翻盖的,很是小巧可爱,丽很喜欢,老嘲笑君的手机难看。相比之下丽比较懂得“保养”,会买一些化妆品,洗面奶、保养霜、唇膏之类的,价格不便宜。丽说:“年轻的时候喜欢用香水,现在也用,我喜欢闻这种味道。”相比之下,君就不用保养品和花露水之类的东西。家里买了花露水,丽的衣服上常有花露水的香味,洗澡的时候也要放上一些花露水。俩人换下来的衣服经常是丽洗,如果丽的身体不方便,君也会洗衣服。
君和丽现已四十多岁,在生理上来说,还没有到性冲动完全消退的年龄,那么她们是怎么解决生理需要的。我曾问过她们这个问题,她们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丽还是说:“年轻的时候过(性生活),现在不过了,老了,不想了。”君笑了笑说:“我叫她去找老伴,她不去,她也叫我去找(老伴),我也不去,我们都不去,晚上看看电视,吹吹牛就睡觉了。”
君还说:“没有她我睡不着,她不在,我就找她没有洗过的衣服穿着睡,和她睡在一起心里才踏实。”丽调侃道:“那是因为有我的味道。”四、对基诺族性少数现象的分析与讨论性少数群体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类型,因为他们的性别认同、性的取向等方面有异于社会中的主流行为,因此一直被视为异类,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但是我们惊奇的发现,基诺山基诺族社会中不但存在相当数量的性少数群体,而且人们对于性少数群体难得的宽容与理解的态度较为友好,社会对于个体性别的认定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们的性取向,同时对性别认同在不同时期的转变也有着相当的容忍度。
相比之下,主流社会对于性别多元的认识是随着当代以酷儿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才得以开始,才对性别的二元分类进行反思,并逐渐意识到应该尊重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可以说,以同性恋为代表的基诺族“考卜拉”性少数文化具有一种优先性与天然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焕然一新的视角。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及社会现象,它颠覆了我们对性少数与性多数之间关系的认知,同时带给我们的是对主流社会中性、性别、家庭及情感更多的反思。
基诺社会流动的性与性别婚姻与性别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尤其对婚姻形式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出社会的组织的结构,也可以了解社会组成的基本方式。而性与性别作为婚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了解婚姻的重要窗口。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往对基诺族婚姻及性的讨论主要在血缘婚的范畴内得以重点
转载请注明:http://www.made-in-yiwuchina.com/hlscf/234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