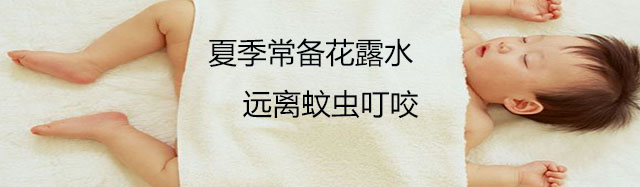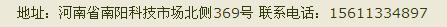这些人死后只剩编号,遗体无人认领,他们会
在殡仪馆大门左边,立着一排公告栏。公告栏右边,则贴着超期寄存骨灰的情况表。盒骨灰在年就应该被家人领走,但是直到年6月12日,遗体依然无人认领。
一些人不知姓名,被命名为胡母陈氏、梁英红之婴、罗北平之B,有人干脆是一个编号,A无名氏。
广州街边流浪汉
然后,他们被挂在“广州无人认领尸体查询网”。照片、死因、死亡地点、身高……简单的十一栏信息,定义了他们的一生。
这个网站属于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是全国第一家公开无人认领尸体信息的网站。广州每年有超过名死者的遗体无人认领,都会在此公示。
根据有限的信息,我们去寻找这些无主遗体生前的故事——
广州市殡仪馆无人认领尸体公告栏。新京报记者罗婷摄
公告栏里
的死者
常住人口超过万的广州城,每年至少要举行0场葬礼。规模最大的广州市殡仪馆,年处理遗体多具,业务量位居全国第一。
殡仪馆主礼楼的26个告别厅在分割好的5个时段里都塞满了悲伤肃穆的人群。
年轻女孩的告别会上,摆着沾满露水的红玫瑰。生前声名显赫的逝者,葬礼会安排在可容纳人的告别厅。
而无人认领的遗体,则是热闹的反面——
在殡仪馆大门左边,立着一排公告栏。左边贴着无人认领尸体的资料。按规定,这些遗体将在公告栏和网上同步公告两个月。
公告栏右边,则贴着超期寄存骨灰的情况表。盒骨灰在年就应该被家人领走,但是直到年6月12日,依然所托无人。
早在年,广州市殡仪馆就曾披露数据,称冷藏库中还有具无人认领的遗体。火葬场则积压着近0具无主骨灰。
没人来凭吊这些休止的生命。他们会被塞入尸袋,被黑色金杯车运到广州市殡仪馆。
接着,他们会被送入殡仪馆的冷藏库,或进入冷柜,或搁上货架。工作人员会把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把面容修饰到至少可以拍照识别的程度。如果实在破碎,他们就不会在网上刊出照片。
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有找到亲属,或是亲属仍不来认领遗体,他们会被包裹着火化。而他们生前的故事,将随遗体一同火化,成为永远的谜面。
广州街边的流浪汉,夜里睡在路边
城中村里
卑微死与生
没人知道去世前,号房的胖先生在出租屋里度过了怎样的五年。
在金紫里直街寻找号房那位先生的家,要穿过隧道一样漫长狭窄的巷子。“隧道”里抬头,只剩一线青天,被乱搭的电线切割成更碎的碎片。
在邻居阿祥眼里,这位先生沉默少言。他每天早晨七点出门,骑着银色的捷安特单车到滨江路,靠向游客兜售杂货为生。
如今那辆车还停在楼梯间,蓝色的塑料篓里散落着圆珠笔、胶布。一小袋莲蓬,已经干枯成灰黑色。房间被上了锁,门上还有他写过的几个大字,“请兄弟无使吵”,这是广东话。
他讲粤语,阿祥听不懂,他们几乎不交流。只有一次,他的手机被偷,借阿祥的手机打电话。他告诉阿祥,自己有个女儿在读高中,但他逢年过节几乎从不回家。
他身高差不多1.70米,“至少有斤”,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常“呼呼”地喘气,看到邻居们吃肉、吃猪蹄,有时会先羡慕,嫌弃自己“只能吃青菜,还这么胖”。
他住的隔断间,一层楼隔开了8间房,每间不过10平米,房租在每月元上下。屋里一扇30厘米宽的窗户,推都推不开,没有一丝风,漏着一点点光。他有时不开灯,只就着这点光在屋内摸索。
这是阿祥所知道的关于号房先生的全部信息。房东则知道得更少,他只在每个月9号上门收一次租金。租房时,他甚至不看租客的身份证。
他死了,阿祥也没嫌晦气搬走,“都是打工的人,哪来的功夫折腾呢。”
康乐中约南新街8巷。握手楼、窄巷子,闪烁的灯牌,密密匝匝的小作坊,是广州城中村的常态。新京报记者罗婷摄
哪里才是
他们的归宿
清晨是广州城一天中最清净的时光。天色刚亮起来,路上行人甚少,珠江的风温润柔软,它公平赠予所有人。
流浪汉们被允许在这里过夜,绿化带将他们与江边的游客隔离开,自成一方天地。垫上被子,幕天席地,至少风雨进不来。天亮后被子一卷,各谋各的活路。
如果细心观察,你能发现“无人认领尸体网”上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从年6月至今的一年间,网站上显示的最高频的死亡医院,几乎每八人就有一人死于这里。
医院离广州市火车站8公里,离广州东站2公里,离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最近,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这些地点都是流浪者聚集的区域。
去年夏天,一位76岁的流浪者在街头被撞倒,不治身亡。这是一位快乐的、有点酷劲儿的老头,穿一条牛仔裤,头发花白,清瘦,收垃圾为生,但床铺永远干干净净。因此人人都愿意亲近他。他来自顺德,有家人,说和儿媳关系不好离了家。别人再问细节,他却不愿多说。
他去世后,义工们在报纸、电视台、微博都刊登信息,甚至通过公安系统查询线索,希望找到他在顺德的亲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出现。他最终被送进殡仪馆,成为无主遗体。
广东顺德的流浪者,去年夏天车祸去世。义工们通过很多渠道寻找他的家人,但他的遗体最终无人认领。受访者供图。
义工梁俭强和流浪者打交道至少5年,他说,有些流浪汉年轻,暂时失去工作,还有机会回归社会。那些上了年纪的,只能靠捡垃圾勉强谋生,疾病、饥饿、意外事件,对他们来说样样都是威胁。
有人给这群人一个残酷的定义:“无人认领遗体后备军”。老无所依,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4月中旬,圣晖园公园的凉亭里,编号A14的男子停止了呼吸。他56岁,东北口音,衣着破烂。他在凉亭里躺了三天,前两天他勉强还能走路,第三天下午已经告别人间。
“嗬,(死的)多了去了。”6月中旬,我到凉亭寻找事件的目击者,这是68岁的流浪汉常双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掰着手指数:“年纪大了生病多。有个湖南的在水果摊边上死了;安徽有个大高个,在上面小牌坊躺着就死了;还有个常州的,坐在桥下闭了眼。”最让他难过的是沈阳的老宋,头一天还和他聊天儿,第二天死在了省汽车站门口天桥底下,“天天喝酒,喝死了”。
义工组织都会沿街给流浪者发放食物、水,有时还会发放棉被。受访者供图。
挽救濒临
逝去的生命
在广州市殡仪馆,负责无主遗体认领工作的是三名女员工。
按照规定,她们只需要贴出通知,达到告知目的即可。但一位员工说,她们其实用尽了办法,尽量与死者的家属取得联系。
一位姑娘已经做了母亲,那些被遗弃的婴儿遗体让她落泪,“你不知道,那些孩子就像睡着了,样子都非常精致,就跟睡着的娃娃一样”。
为了让这些无主尸体能得到妥善处理,广州市公共财政每年都要投入近万。
年2月,《广州市无人认领尸体处理办法》正式制定出台,对无人认领尸体的处理善后有了明确规定。
实际上,确实有少部分遗体最后会被家人领走。一旦网上公示的信息被撤下,就意味着这具遗体等到了来处理的家人,将免受孤独之苦。
6月上旬,18岁女孩梁巧红的信息就从网站上撤下。
4月17日她在海珠区的一个小区去世,死因待定。她妈妈来领走了她。在殡仪馆的业务大厅“天堂信箱”里,我们看到了妈妈写给她的信:“亲爱的梁巧红,妈妈带来靓靓裙、高高高跟鞋,让你美美上路,去极乐世界做善良天使。”
我们还找到了两个感人的故事。
今年端午节前,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陈婧接诊了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婴。她的母亲疑似精神障碍,养了十几只猫,把猫看得比孩子还重。她对孩子又掐又捏,一直嚷着要把她打死。医院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全身是血,满是淤青。
急诊科的护士照顾了女婴五天,给她买了奶粉,洗了澡,妻子在哺乳期的男医生,还带了母乳来喂她。她很快恢复生气,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人。她最后被送到福利院抚养。
年10月,流浪者韦士带躺在人民路的高架桥下,已经不能动弹。他臀部已全部溃烂,患有严重的肝吸虫,左手关节和膝盖都被肿块撑得变了形,紧紧裹在被子里。义工来看他,他一心求死,只要一瓶烧酒。
几个男义工扛起他放上三轮车就走,烧了热水在公厕给他洗澡,医院。之后他病愈,回了广西横县老家,结束了流浪生活。
此后五年,上百位义工开始沿着广州城的大街小巷给流浪者派饭。夏天派花露水、蚊香,冬天派棉被。团队里有医生,还有成员负责给他们找工作。
韦士带回家的那个冬天,义工梁俭强在复方木尼孜其盖博士盖百霖哪个药物有卖
转载请注明:http://www.made-in-yiwuchina.com/hlsjw/147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