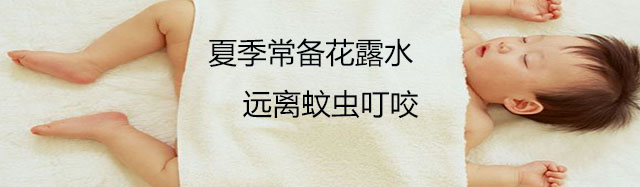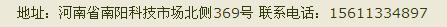风逸杯作品征集中丨听陪伴的声音风中有朵
风逸杯获奖作品展
散文组一等奖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徐慧杰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一朵雨做的云,
云的心里全都是雨,
滴滴全都是你。”
人生,缘始于“遇见”,情长于“陪伴”。
人总在孤独的苦旅中,愿你我停一停脚步,彼此做伴。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前记
在遇见她之前,我一直好奇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会怎么样,是子孙满堂还是多病卧床?
也许是岁月的冷峻,我常常感受到她对待生活是一种既乐观又悲观的复杂态度。可能大多数人老了之后都会有一种悲哀,身体机能的下降,导致自己只能困在床上,无论做什么都要靠别人,甚至因为活的太久,亲人、朋友都先自己一步而去,自己虽然还在活着,但实际上已经在逐渐被世界遗忘。没有人不想活着,但是孤独有时也会让人绝望。
有个志愿者向我回忆,奶奶曾说过“不要忘记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俄语妈妈”。我曾听过一种说法,死亡有三个层面,身体上的死亡,社会宣布的死亡,以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的死亡。如果一个人活得太久,久到没有人记得Ta是谁,死亡便会直接从第三个层面开始,从灵魂上走向地狱的黑暗。
一个人如果长期闷在房子里,不和人交谈,往往很容易出现精神问题,而志愿者们希望能为老奶奶做的是给她更多的精神陪伴,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着她。
甚至夸张点说,她们是在努力的和死神作斗争,希望能够延缓老奶奶的精神死亡。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归属感、渴望陪伴的何止老人。虽然说孤独是人类天性的必然,但是还是希望我们能记得,给身边的人一点关心与陪伴。如果说,“无穷的人们,无穷的远方”对我们来说太难,那么就从身边的朋友开始吧。
我想纪录下这场短暂的相遇,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她生命的过客。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渴望陪伴的人们。
1、来自东北的混血奶奶
那时已是初冬,屋外的花几近残败,屋内的绿植依然郁郁葱葱。我大约再难忘记她紧握着志愿者的手,念叨:“你们、你们要常来啊……”的场景。
屋子不大,四个小房间组成了她的家。客厅的柜子下面是护工小袁阿姨为她买来的水果,桌子上是她常念叨的“cake”。客厅的陈列柜上则满满的承载着她的回忆,许多大大小小的相框错落有致的立在陈列柜上。
岁月刻画在她的皱纹里,也留存在这些珍贵的照片里。
就像她的血统那样,她的家充满的中俄融合的味道——中式的木衣柜、俄式的花壁帘。
上世纪东北的边境,一位美丽的白俄罗斯姑娘跨越边境线,在中国的大地上诞下了一个混血女婴。
高奶奶的俄语便是遗传于她的母亲。直到现在,高奶奶依然保持着对俄语的热爱,她平时最爱说“спасибо”(谢谢)。有时她也因此很苦恼,“唉,其实啊……说俄语对我来说最方便,要是俄语,我还能多跟你们聊聊”。然而,身边很少有能用俄语与她交谈的人。
“cake”是高奶奶的最爱,午睡起来,护工小袁阿姨为她端上一碗蓝莓夹心的“cake”。高奶奶行动不便,于是一个塑料瓶插上吸管——便是她的杯子。
高奶奶也常常念叨“圣诞节”。她爱过节,爱热闹。若是有人用手机给她放俄语节目,她会立刻精神起来。可这是不常有的,家里的电视大都是中文。事实上,高奶奶的腿已经动不了了,打开电视对她来说也是困难的。
“你这耳坠儿厉害。”高奶奶对来看她的志愿者说。郭滢是离她最近的志愿者。听到高奶奶的夸奖,郭滢俏皮的晃动她的金色耳环。
“好看,好看。很有面子。”高奶奶感叹道,“我也有耳洞……年轻的时候有,现在都长上了。”
“你们穿着也讲究,好看。”
“好看,那我们给您也买一件?”
“也行,这颜色我敢穿。”
高奶奶喜欢素色,“因为我岁数太大了,年轻的时候也穿鲜艳。”
“我老头儿也好打扮……从日本回来的也是,穿的很讲究。”
她的右手带着婚戒——一个素雅的银戒指,在那时,算是新潮的。
她的丈夫张厚璁,那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们俩是在溜冰场上认识的,都爱穿西装,“我不穿旗袍,只有一个作纪念的”。
“从心里说,青年人,个个得精神,这一定,外表得像样子……必须记住,精神太重要了。”
她没有孩子,她那说日语、会溜冰的“老头儿”也去了。小袁阿姨是她身边唯一的人。
除了小袁阿姨,有时她的学生也来看她。再有,就是那些志愿者们。
“头发梳漂亮一点。看,他们都穿的漂漂亮亮的。“小袁阿姨帮高奶奶梳了梳头发。“你也漂亮一点,是吧?”
“спасибо,спасибо。”
“啊?”
“Thankyou.”她又说了一遍。
“我们听着是‘快去吧,快去吧’”。志愿者们都笑了。
志愿者们来自青年志愿者协会,他们通过“鹤童项目”他们共同相聚在一处藏在树荫下的家属院。
陪奶奶聊天,和奶奶一起唱老歌,是每周的“固定话题”。在这个有些幽暗的小房子里,他们努力为高奶奶带来阳光和欢笑。
“奶奶,我们刚刚看你照片呢。”“好看。”“还化妆呢。”
“年轻,还能站着。”高奶奶叹息道。
2、风中的歌谣
“不能随便出来,老闭眼睛。”
她腿脚不好,眼睛也看不大清了。但是生活中总还有些快乐。
“高兴,高兴,有人惦记着。”高奶奶一直拉着郭滢的手,并多次的用俄罗斯的礼节亲吻郭滢的手背。
“难得,天天窝在家里头……因为我年纪太大了,比谁都大吧?”
“那可不是?”
“大的我都觉得已经过多了。应该……即可而止了。”
“您还得创世界纪录呢。”郭滢宽慰她。
“但愿如此。”
“高万里同志,创世界纪录——”郭滢笑着为她打气。
“我是卖衣服的服务员,所以我很知道衣服时髦不时髦。”
最初的时候,高奶奶并不是俄语教授,而是一个在战乱中讨生活的混血姑娘。她做过许多工作,卖衣服的服务员,广播电台的广播员,“主要是为了讨生活。”
那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她的日语就是跟日本人学的。就像高奶奶自己说的那样,边工作边学习就是她的本事。
“日语,向日本鬼子学的,过去还挺尊敬,后来看小日本就超恨了。”也许正因如此,她的弟弟去参了军,作为一名新四军跟着共产党打仗,为解放家乡而斗争。
“那时候东跑西跑,就很贫困。你看你们多好,多出息,一个一个的,都精神。”
“我们是时代好。”郭滢对高奶奶说。
“必须记住,精神太重要了。不管怎么样,都得让人看看,我是在大学的。得有味儿,没味儿不行。”
高奶奶精神已经不大好了,所以也最看重“精神”。
每每在聊天的时候她觉得没精神,志愿者就会提议给奶奶唱歌。
“历经沧桑魂牵你我,心中装着那汉武的踪迹。你那天堂寨的美丽,造就了多少神奇。你那血一样的河流,强壮了多少好儿女……”
高奶奶喜欢听老歌,最喜欢听吕继宏唱的《大别山》,那天她不断对志愿者们说:“最爱那个大别山,一哼哼就有劲儿了……战士劲儿就出来了。”
她没穿军装,但她的丈夫张厚璁确实是一名军人。她说,她那时是电台的广播员,全省唯一的俄语广播员。后来,才辗转成了外国语言学院的俄语教授,渐的方法才渐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
她说,最拿手的就是俄语歌,《Подмосковныевечер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Катюша》(《喀秋莎》)都是她年轻的时候爱唱的。
高奶奶爱歌也能从照片上看出来。她的陈列柜上有一张照片便是她与歌手杨光的合照。他们都是东北人。
3、来自南昌的小袁阿姨
小袁阿姨是南昌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是干活相当麻利。
每次高奶奶起床,她总要给高奶奶先量个血压。
“高压还行,低压有点低啊。”她捏着血压计喃喃道。
高奶奶腿上使不上劲,上厕所都是用一个座便器。无论是上床下床还是上厕所,都是小袁阿姨一个人把她抱起来。抱奶奶上厕所是不容易的,没有经验的志愿者七手八脚两三个人才合力帮高奶奶坐上了座便器,而平时,这项工作都是小袁阿姨一个人完成的。
奶奶的家很小,但是胜在干净整齐。厨房的墙壁是雪白的,柜子上也没有污垢,锅碗瓢盆错落的放着。卧室的小柜子上也是整整齐齐,维生素E乳、痱子粉、花露水、碘伏消毒液……像列兵一样齐刷刷的立在小柜子的收纳架上。
高奶奶和小袁阿姨的关系很好。她有时午睡不愿起床,小袁阿姨便会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不起来?你不起来我走了,我回老家啦……不起来?我回老家啦,我回南昌哪!”
“明天去。”
“你老睡觉,你不起来陪我玩……那我回去了,你行不行?”
“行。”
“真行啊?“
“可以。”
“那我走了。真走了。要你一个人睡。那你起来找不到我了……我坐火车去,我回老家去。”
“别……”高奶奶终于败下阵来。
“啊?不要去?那你不起床你老睡啊。睡多了你晚上又折腾人,白天不能睡这么多。”
“我不折腾,不折腾。”
“那咱不睡了?“
“好“。
有时,她就像个孩子,晚上不睡,白天赖床。
“我能走还能走,就是一天儿,眯着最多。”高奶奶承认自己也有不规矩的地方,“人家批评我了,我接受,好好睡觉。”
“cake,有的节日能买,有的节日不能买,我就跟着国家走吧……国家是主人,他们做主。”
在高奶奶眼里,小袁阿姨也是“主人”。
“谁批评你啊?”志愿者们问她。
“我的主人。”她说。
她爱着她的两个“主人”,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依赖让她像一个纯真的孩子。
4、万里晴空或是乌云密布
高奶奶很喜欢志愿者来看她。“也难得有这时候,不能老昏啊……唱唱歌,就有中气了,不像我,老了”。
“老了也好看,就能看出来您年轻的时候有多好看”
“还行,还行。”高奶奶有些谦虚,“спасибо(谢谢)。”
高奶奶喜欢看好看的男孩、女孩。看到漂亮姑娘她就会忍不住夸两句。看到志愿者给她放的视频里的漂亮男孩,也会赞叹道“好看的男孩……”,甚至对于视频中的指挥也多加赞赏:“这老头儿也不错。”
“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什么好看穿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不穿才是傻
子呢。”
她也爱听韩磊唱歌,称韩磊为“那老爷们儿”,说:“那老爷们儿歌好。”她记性不好,常常记不住人,但对喜欢的歌手的名字,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她努力寻找这世间的美好,只是生活总有些如意和不如意。丈夫的离去,让她常常感叹“没有他不行。”而更一步步蚕蚀她的,是时间。
“老人吧,常常遇见这些,不能不防,该病就病,该升天就得升天……我也快升天了。”
衰老逐渐将她从这个世界中剥离,腿脚不便,视力模糊,一切机能的衰弱都让她觉得恐惧,甚至有时她会想到自杀。“我和你们不一样,死去了的心,什么都做不了,除了自杀。我能感受到那一天来临,但我不害怕……就还不归天,就还得活着。”
她也渴望被记住,她说,希望志愿者们不要忘记她,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
有一个俄语妈妈。
“奶奶可重视仪式感了。”郭滢说。
走的时候,她亲吻志愿者的脸颊作为告别。
“希望你们常来啊。”
陪伴不喧哗,自有声。
陪伴是最温情的语言,生活漫漫,让我们细细述说。
赏尽风采,不妨下笔一试,书写自己的风神隽逸!
第七届首都高校“风逸杯”征文大赛参赛须知
本次比赛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会、首都高校中文联盟联合举办,面向首都高校大学生广泛征集文学作品并进行评选。参赛选手须完成比赛资讯邮箱里的报名表,并将报名表和参赛作品于年7月16日24:00前一同发至投稿邮箱,报名表上必须注明联系方式与银行卡号。
咨询邮箱
账号:fyb04
.转载请注明:http://www.made-in-yiwuchina.com/hlsxg/24544.html